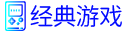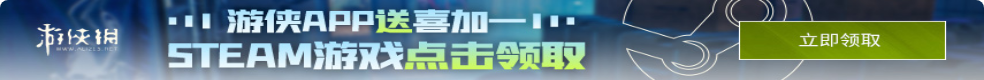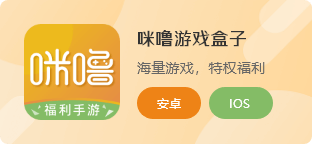45岁的穆哈里卜蹲在帐篷门口搓着冻红的手,塑料布被风扯得哗哗响,她盯着远处废墟里露出的半截墙——那是之前家的位置,现在只剩钢筋戳在沙地里。“听不到响了,可总觉得耳朵里有回声。”她把小儿子的头往怀里拢了拢,孩子攥着半块硬面包,嘴角沾着面渣,“昨天夜里他突然喊‘妈妈跑’,我抱着他哄了半小时,才想起现在是停火期。”
这是加沙停火的第14天。从10月10日协议生效至今,空中的硝烟散了,可地面上的“日子”还卡在“生存线”上。19日的空袭像根刺——以色列说“回应士兵被射杀”,落在加沙南部时,穆哈里卜的帐篷都晃了,“我抱着孩子往桌子底下钻,等反应过来才想起‘停火了’,可那声爆炸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吓人”。更让人心惊的是汗尤尼斯的无人机袭击:纳赛尔医院的医生说,一名巴勒斯坦人被当场炸死,以军称“清除”,可住在“黄线”附近的居民早成了惊弓之鸟——他们刚被要求撤离到以西区域,废墟堆得连路都没法走,背着水桶挪步时,谁都不敢抬头看天空。
比恐惧更熬人的,是“饿”。穆哈里卜的帐篷里堆着两袋救济粮,一袋是干得掉渣的面包,一袋是泛黄的豆粉,“每天煮一锅稀粥,放一把豆粉,孩子能多喝两口”。47岁的扎库特扛着空水桶往取水点走,鞋子底磨出个洞,沙粒灌进袜子里:“废墟把路堵死了,要绕三公里才能接到水,更别说吃的——商店货架早空了,救济粮要排三小时队,有时候还领不到。”
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比这些场景更戳心:2025年以来,加沙已有411人死于营养不良,其中109个是孩子。“这些死亡本可以避免。”世卫人道主义负责人特雷莎·扎卡里亚的话像锥子——协议里说好的“每天600辆援助卡车”,实际只有200到300辆进加沙。谭德塞在日内瓦摇头:“这只是所需的一小部分。”穆哈里卜领到的面包是三天前的,“硬得能砸开核桃,可孩子饿,啃得直咧嘴”;扎库特所在的帐篷区每天只能分到两桶水,“洗了脸就没法做饭,只能省着用”。
更让人着急的是,外界连“看见”这场挣扎都难。国际记者想进加沙采访,以色列最高法院拖了又拖——哪怕外国记者协会提了请求,法院还是给了政府30天“明确立场”的时间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说“这是拖延战术”,可对于穆哈里卜们来说,没记者进来,帐篷里的哭声、取水路上的背影、医院里孩子虚弱的呼吸,都成了“没说出口的痛”。
风卷着沙粒打在帐篷上,穆哈里卜把绳子系得更紧了。她摸着口袋里的救济粮券——那是明天领粮的凭证,“希望能多领一袋豆粉”。远处传来卡车的声音,她抬头看了眼,又低头揉了揉孩子的头发。停火后的天空很蓝,可蓝天下的日子,还卡在“活下去”的坎儿上。
没人知道这场挣扎要熬到什么时候。穆哈里卜只知道,明天得早起去领粮,得把水省着用,得哄孩子不再做“跑”的梦。爆炸声歇了,可生存的硬仗,还没歇。